我是星辰下田野中的一片碎瓷
发布日期:2013-02-28 来源:市委统战部 浏览次数: 字号:【大 中 小】
我是星辰下田野中的一片碎瓷
——由《马兰谣》简析张健的诗歌创作
傅元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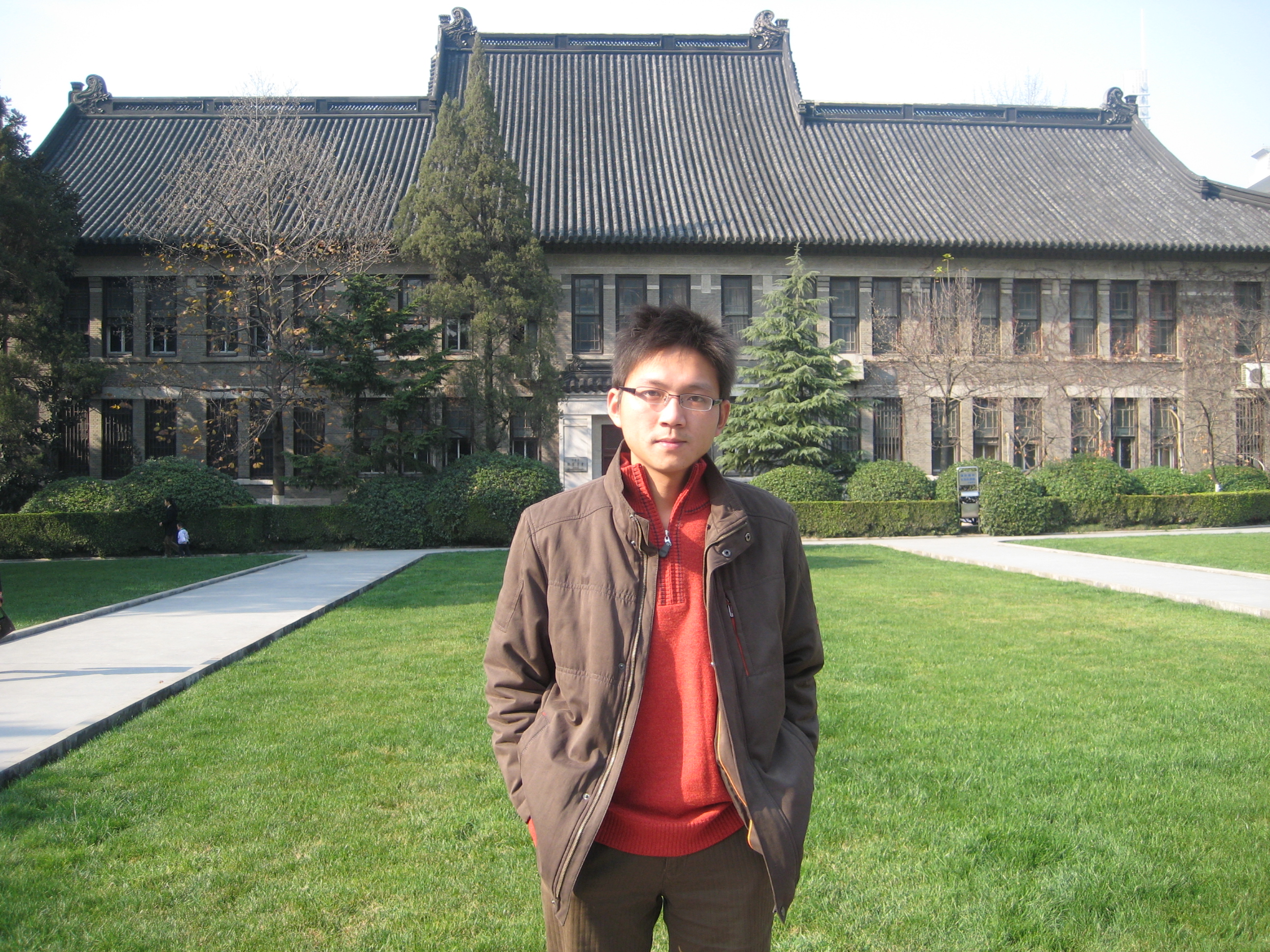
读张健(笔名张羊羊)《马兰谣》,意绪变得沉缓,安静,时有灵魂的自责。勇于代表文明的自我反省,对生物和农业的家史般的欣赏,对亲情的依恋和歌颂,对童话和女儿国的倚重和呵护,这些张羊羊诗歌的原质,依然弥漫在《马兰谣》中,它们让我进入了纯净的语言和心境;让我自责的,是张羊羊锐化了的童心和混沌之间的矛盾冲突,是他的让人敬畏的纯真和一贯的敏感。我深深感到,他对生命衰颓和消泯的洞悉和由此衍生的忧伤甚至愤怒,在我的精神生活中,较少存留。
相比《从前》,从动物和植物、亲情和农业的发酵物提纯的酒精依然掩护着童话:“我是安睡的婴儿/……/我是将成年的父亲/满嘴酒的芬芳/长成老者的是树/变回孩子的是奶奶”(《关于我的故乡》)。在氤氲的故乡沉醉中,“夕阳想穿我的小布鞋”(《水乡谣》)这样的句子,是屡见不鲜的;“我写下的每一个字/都是爱的异体字”(《我的日记本》)。这是羊羊诗的常态。不同的是,纠结和忧伤多了,羊羊在《马兰谣》梦境般的迷醉中,深埋了更多成长的忧虑和哀伤。
张羊羊的“童心”是一种独特的诗歌结构:“用清晰的田野/和发芽的星空/填满我空旷的心灵”(《大地的孩子》);“花狗在梦境里/和我的少年再次相遇”(《庭院》),只有童话,主体的出发点才会是一只小花狗,自我是客体;羊羊的主体自省方式,是将自我处理为生物王国里横陈的无机物:“我是星辰下田野中的/一片碎瓷”(《当我想起》);诗人的主体自信也有特殊的逻辑:“我们永远是水孩子、雪孩子/纯洁、不死/像野花的眼睛一样真诚”(《小小的情歌》);童心是一种看似轻率的献祭,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任性和固执:“我,一个不太纯洁的穷人/没有和那些鸟一样/遵守曾经的约定/在大地短暂的一生里/我用一粒土的身体去喂养/胡萝卜那橙黄的挺拔的忧伤”(《记忆之伤》);一个童话抒情者,永远也长不大:“现在我们快七十了/我们讨论着/临死前还有没有机会长大”(《聚会》);童话诗人或许都会像顾城那样,从“道”之原初与婴孩礼赞中获悉自己的未来:“世界明亮了/我从简约的时光那/再次领回婴儿的身份”(《小忧伤》);他们也会秉持生物性的民主,“想和一只茄子/交换生活理想”《蓝色理想》,“我对荒野充满感情/每看一眼会自卑地转身”(《小王国》)……
如果没有真淳的灵魂,是唱不好一曲童谣的。在诗歌地理学上,心理童谣应该是一种南方文体。“在我私人的南方/三月细雨,桃花零落/我种过的蓝色之梦/沿篱笆长出了触角/我修剪童话,收藏悦耳”(《南方》)。羊羊的诗在自我修剪中,增加了南方的忧伤,又时而带有北方凌厉的刺痛。
曾经以为,羊羊的诗歌将最终向童话诗的方向前行,但《马兰谣》的主体风格,推翻了我的预言。有很多稚气十足的简单诗句,交由深受当下语文教育之害的孩子理解,必须加上冗长的注脚。他的诗,有一种独特的心灵文体。其秘密或许在于,“一个把童话读成巫术的人/清澈地获知了来历”(《羞愧》)。因为这种清醒,羊羊的诗中有悲愤和决绝:“也许已是时候/请容许我收回过去多年中泛滥的抒情/在某个黄昏忘却滑稽的微笑,果断撤下伪证”(《一份总结》)。
在羊羊的诗中,有些痛感很强,显示出他的童话王国里蔓延着痛苦这种植物,“现在我每看见日落/就像受一遍绞刑/就忍不住预演一遍怀念”(《母亲》),痛感侵蚀着梦境,让纯美的抒情富有情感的张力。在《倾诉》中,他甚至写道:“采两朵木耳给我吧/当我无法歌唱恩与情/请你用最后一根针线/缝好我的嘴巴”。我曾经建议他将最后一句删掉,但转而意识到了他的耐受力来源于纯粹的情感。他能决绝地遗弃坏死的自我,慈母游子的和谐针线,已经不属于此刻的美学。做了父亲的羊羊变得宽容,以致容忍阴郁和悲苦在他的王国中攀爬过了心灵的窗棂,长出了茂盛的叶子:“我的舌尖上/悬满蝙蝠/在昏黄的故园/随黄鼬漂泊/祖先啊,我自此寻找/泥土和水源/悲苦如蚂蚁/翻越一座大象”(《蓝花》)。他在《口述》中写道,他的生命王国虽则和美,但边疆一直都有宿命的鏖战,“此地不宜久留”让基于生命边沿的自足和忧伤在诗中缠绕,富有韵致。
时间的倒置,身份的交互和空间的错位,在《马兰谣》中俯拾皆是。这种诗歌构图基本是由他心灵童话的想象力决定的,但也与他精神成长的哀矜情怀密不可分。“我时常用快乐的心情/想悲伤的事/我最好的朋友/是酒唤回来的逝去光阴里的我/我和我的部分擦肩而过/或许也会握手也会微笑”(《美妙》),这种童趣对忧愁的化解,很多时候并不分清到底是谁占了上风。诗人也会间或承认:“我快被悲伤淹没了/那驼背的老杨树/仿佛与我互悼/那怀想稻草人的/三两只麻雀/在平原静静发呆”(《回乡偶书》)。
马兰之歌,多有其悲。我在《马兰谣》中体会到了《从前》中鲜有的告别口吻,“请种下我深爱的马兰/她灿烂的微笑/像一枚小小的悲伤/这里没有内容/路过的人请不要张望”《马兰悲歌》。在最后一句,诗人对世俗和路人有一种不加掩饰的失望,主体拥抱了马兰,竟决绝将自我孤立,隐逸自绝于尘世的意绪漫溢。羊羊的诗歌世界还保留着自我的圆满,这让诗集有暖色调,最终成其为“谣”。
我喜欢“谣”这个字。《诗》有云:“心之忧矣,我歌且谣。”真纯的歌哭,没有丝竹混杂的肺腑之音,让“谣”有万种风情。在中国,谣之为诗也久。近百年前,老北大的《歌谣周刊》与新诗的亲子关系,虽至今还未得到确切的诗学鉴定,但对那些歌谣及其收集者的敬畏却是多了起来。与此同时,在启蒙主义与拜物教的双重挤兑下,童谣乡曲的亡佚已是不争的事实。一句乡谣,传得古旧了,往往就不再是可译的言语,会附加诸多音乐的成分,甚至会成为神秘的图腾和象征。诗歌意义的隔膜,往往产生在语汇的错觉。在自负的硬译面前,诗有时候很难抵达一个心灵的居所。这个时代,理解一句格言很容易,听到或听懂一声童谣却是难上加难。
行文至此,耳边尧十三的歌谣《瞎子》正以民谣的方式向柳永的《雨霖铃》致敬:“现在是秋天嘞/我一会酒醒来/我在哪里/杨柳的岸边,风吹一个小月亮……”风吹一个小月亮。尧十三,张羊羊,似乎不约而同压上了一个神秘的韵脚:“小小的马兰花/从风里寄来紫色的小小的呼吸/小小的太阳啊/一指指丈量小小的故乡”(《马兰谣》)。因为他们,当代疏落的民谣和苍白的心灵,还是聚拢起来,有了一些弥足珍贵的饰物。 (农工党常州市委组稿)
链接:张健,笔名张羊羊,1979年5月生于江苏武进。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。中国作协会员,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。农工民主党党员。作品散见于《钟山》《天涯》《散文》《诗刊》等刊物。有诗集《从前》《马兰谣》,散文集《庭院》等出版。现供职于武进文广新局创作室。
 当前位置:
当前位置: